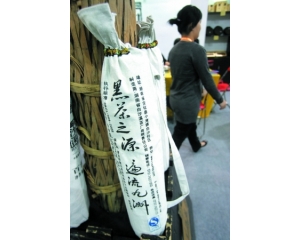他泡自己的碧螺春给我们喝,由于茶叶极细,所以先倒水后放茶叶。茶叶本身内质好,很快都沉了下去,幽静地在水底舒展开来,瞬间茶汤碧绿。“在苏州喝碧螺春讲究用粗瓷大碗,因为茶叶很细,这样就碰不坏叶子。”不过,现在还那么讲究的很少了,“北方人因为对绿茶少了解,只知道龙井和碧螺春,也以为这两种绿茶属于特别香的类型,可是他们喝到的,往往是按照这两种工艺制作的类似的绿茶而已,并不是正宗的原产地茶”。
在原产地去寻觅好茶,肯定是一种相对可靠的方式,吴海峰说他自己周围的一帮朋友都这么做,不过前提是你要懂茶。“现在去杭州龙井村买茶的人那么多,可是有几个能买到真正的好龙井?大多是各假冒地拿过来销售的。”
吴海峰的朋友林曦是个女画家,平时生活在草场地自己设计的大房子里,喝茶,玩沉香,也弹古琴,用定制的毛笔宣纸作画,虽然还不到30岁,可是生活得浑然如古人。早上起来不把茶喝透不出门,特制的茶桌上,放了10多个茶杯,泡不同的茶喝。
她的茶龄非常长,从12岁就开始自己在家泡茶喝,拿出照片,梳着长辫子的她正在给濮存昕一家泡茶喝,似模似样地摆了一桌茶具。她告诉我,她和母亲各有自己的一套茶具,从她小时候开始,两人就各自泡各自的茶喝,这已经成为家里的重大习惯。“我男朋友第一次去我们家,就看见我和妈妈整天对坐泡茶喝,别人家是玩麻将度日,我们家是喝茶过日子。”
从小时候开始,林曦就有到原产地找茶的经历,很多美好印象也都发生在找茶的过程里。“十几岁的时候,和父母亲到杭州,别的地方都不去,只奔龙井村,早上就去了打听好的几家茶农家里,一家家地喝过来。”那次泡的龙井清澈得近乎透明,不是那种不好看的绿色,喝一口,香浓得至今难以忘记,这是绿茶留给她最美好的印象。去武夷山更是这样,因为相比起清爽简单的绿茶,老茶客林曦现在着迷的是岩茶。
现在没那么多时间去外地了,“基本上就在北京各个熟悉的茶叶商人那里晃,一般坐下说几句,别人就能够根据你的谈吐判断你的需求,不会拿很差的茶给你喝”。她的标准是,一定要喝过才决定是否是好茶。在林曦看来,太多人是用耳朵和眼睛喝茶,不是喝茶叶本身。圈子混熟了,就有茶商经常主动打电话过来,“刚到了一种好茶,你快来帮我品评一下”。这种混圈子是保证能喝到好茶的基本功。
不问出处的好茶
用耳朵喝茶肯定是现在的流行病,叶羽晴川将他一个朋友的故事给我听:“他从贵州那里拿到了几百斤上好的都匀毛尖,也是十大名茶之一,可是北京人大都不熟悉,结果很久卖不掉。后来有个似懂非懂的买家去那里,问这是不是碧螺春,两种茶看上去很像,结果我那朋友多了心眼,没说真话,这批都匀毛尖陆续被当作碧螺春买走了。”
叶羽晴川原名叶朝武,本在四川一家出版社当编辑,10年前,被同事鼓动着写了本关于茶叶的书,用了这个笔名,“结果一发不可收拾,就此爱上了茶”。现在他已经有10本茶书问世。“主要办法就是去产区喝茶,中国出好茶的地方就是几大山脉,所谓的北纬30度地区,我几乎是一座座山头那么摸索过去的。”他说自己的好处是,不会找茶叶商人索取什么,最多就是一点茶样,这样就敢于在书里任意表扬或批评某茶,建立了自己的公信力。
他不赞成一定去某地找某茶的想法,也举了龙井村为例子:“现在的龙井村因为茶科所的推广,基本上都是用的改良种,产量高,香气差多了。所以即使是去那里,也不一定可靠,还不如去认识一些可靠的人,那样喝到好茶的机会更高些。”有一年,他喝到浙江大佛的一个老农送来的新龙井,“完全改变了我对龙井的印象,喝一口就呆住了,怎么这么好喝?是不是加了什么东西?”大佛是龙井的新产区,一般人总是说那里的龙井比不上西湖的。
所以,叶羽晴川赞成把视野放宽,“不一定非要在有限的资源里面去分一杯羹,应该去挖掘新的东西”。因为有限资源的理论而上当,买了很差的茶叶的人大有人在。
他赞成去蹭茶,“好在现在所有的茶叶店老板都会拿茶给你试喝,那些茶也许没他吹嘘的好,可是你要是有耐心,一家家慢慢品评,总能找到最好性价比的茶叶”。他现在在外面讲课,一直鼓励听讲者学会“蹭”,“不靠自己的嘴巴,听人家说的怎么好都没有用”。
因为四方游走,也多了不少喝好茶的经历。一次是在湖南湘西一个小县城,主人是个退伍军人,又去大学进修了制茶课,那年春天两人碰上,主人精心做了几两好茶,“没什么名气,也没什么花样,结果一喝之下惊叹不已。主人一定叫我提意见,我喝了半天才说,我觉得好像你做到后面太急于求成了,总想把这茶做到最好境界,所以火候有点小问题”。其实也是鸡蛋里挑骨头,不过两人越说越高兴。主人告诉他,只做出了几两,县长来买,主人说是再高的价格也买不到,“不是故意想吊人胃口,而是极品好茶不是靠人力就能得到的”。
好茶多为可遇不可求。“上次在浙江一个小茶馆,喝到极好的茶,问起来也是一个老师傅刚做出来的,只有4两,老板总共就1两,我怎么说让他分我一点都不干。”
这种好茶不问出处的道理,在台湾画家罗建武那里早就悟透,他对我说:“我买茶只管茶好,也不问产地,也不听人家任何宣传,最好的茶,往往来自于意外。”
老罗被称为“茶痴”,在台湾教学生的时候,因为一个学生的父亲是台湾最著名的茶专家而与茶结缘。“那些年像得了病,四处寻找好茶喝,而且经常为了茶的好坏和人争吵,结果别人笑我不是在找茶,是在找碴。”他的日常生活除了绘画,基本被茶所占据,最极端的例子,是把连续几年台湾拍卖的名茶冠军都买下来了。外界说是会升值,其实他哪里舍得卖?展览给我们看,瞬间堆满了桌子。
尽管四处寻觅,可是给老罗留下美好印象的绿茶也就是两回。一次是在黄山上写生,在汤口附近的农家喝到的野生毛峰,“外形很难看,根本不符合毛峰标准,可是喝起来才知道好”。问起来才知道,这些茶来自最高档的毛峰核心产地的边上,“也是终日云雾缭绕之地”。
还有一次是喝碧螺春。老罗自己手上有些好碧螺春,据朋友说是苏州市领导送的,转赠他一点,结果拿给另外一个朋友喝,那朋友当即斥责,说你这算什么好茶!老罗当然不服输,去朋友那里见识他的碧螺春,一喝之下,“也没多说话,因为知道天外有天的道理”。
讲究产地出处的吴海峰也宣传一些无名之茶,他抖落自己手中一些不怎么好看的炒青,在他家乡被叫做菜茶的(因为不值钱,就像菜一样),这些年没人精心栽培倒越来越好,10多块钱一斤的茶叶,居然和几百块一斤的龙井不相上下。“关键还是要看自己的需要。” (责任编辑:占万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