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大早,从pedro出发,翻译说去斯里兰卡茶叶研究所!
途中,山路崎岖,弯弯曲曲,惊险无比,好几个急转弯路口,大巴险些搁浅,是司机的高超技术,最后都是有险无惊。
一路都是漫山遍野的茶园,以任何的角度去取景,都会是一张张美图。车窗如画,面对呼啸而过的一幅幅美丽的图画,你根本来不及作仔细的欣赏。对美的麻木,是精神层面的另一种奢华,麻木了的审美,是无趣的开始!对艺术家而言,司空见惯的审美疲劳,没有了激情,这是很可怕的艺术创作的休克与死亡!
他们也司空见惯了,途中没有让我们停留一下看看我们喜欢的茶园。
斯里兰卡茶叶局的一位陪同非常尽职地用英文介绍着一路所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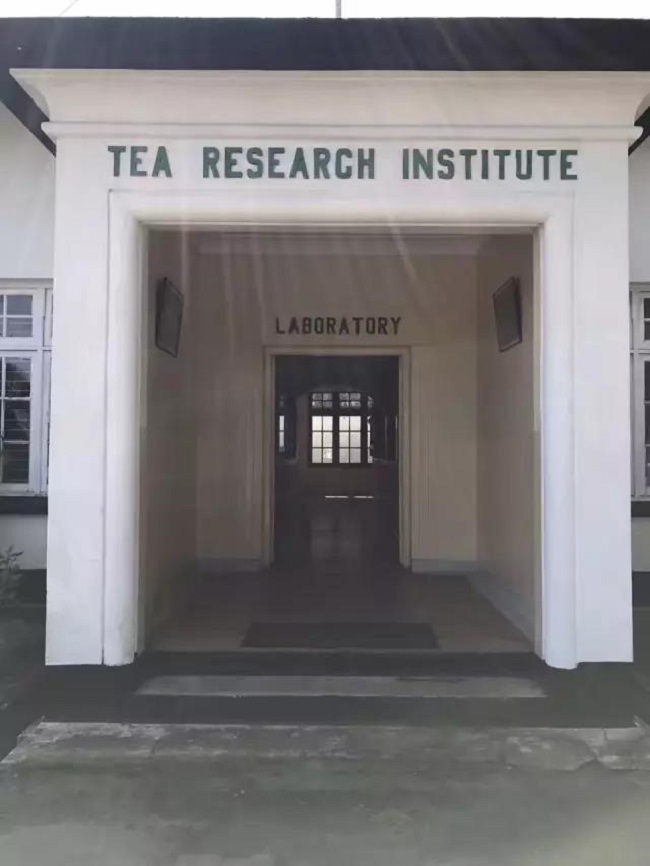
到了斯里兰卡茶叶研究所,直奔会议室。所长大人一定是把记者当专家了,全盘托出,毫无保留地交流,研究所各个部门轮番上阵介绍,这情形有点像咱们的组织部去开座谈交流会,考察提拔干部!
斯里兰卡茶叶研究所成立于1925年,是斯里兰卡国家种植业部的一个分支机构,总部位于塔拉瓦卡类,在不同茶区设有5个分部,设有农业经济、农艺、昆虫与线虫、生物化学、植物育种、植物病理、土壤与植物营养、加工技术、推广等研究部门,主要针对斯里兰卡茶叶生产需求开展研究。

至今天,茶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健康饮料,全世界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种植生产茶叶,有170多个国家和地区销售和流通茶叶,有20亿人饮用茶。但是研究茶的机构基本上在生产国。各大生产国对茶如何经过无性系繁植优选品种以及如何利用土壤、植被等生态环境小气候来提升自然品质还有应用创新技术创新工艺来提高品质质量等等方面,各有建树,成就已现。近几十年来,包括中国在内的茶叶生产国科技技术攻关的命题被食品安全被农残牵着鼻子走,由于茶的需求关系长期处于买方市场控制,市场的话语权也偏向买方。包括联合国粮农组织茶叶小组,国际茶叶委员会在内以及一些消费国的茶叶组织如欧盟、英国、德国、美国等西方国家在进入21世纪后无不加强或提高了农残监测标准,他们关注的更多的是消费者这头,而对生产者源头的艰难、无助甚至因无法执行过分苛刻的标准而产生的绝望,没有以国际性全产业链的视野或者说是完完全全以良好农业的道德标准作超越利益关系的行业问题的关注。赚足了钱的代理商和世界茶叶品牌商自己一味地逃避责任,把所有的责任留给了生产方。对于个别指标不合理的申诉,制订标准方自己拿不出安全性评价的数据,却要生产方来提供等等,这些问题的讨论与沟通不是在一个平等的层面……
所长大人完全可以借这样的机会与有点像联合国组团的各国茶媒体记者谈这些问题,当消费国的茶协会组织听不了生产国的意见,当代理商和品牌商以买家的身份高高在上你无法与他沟通,专业媒体的记者站着公正的立场上也许会听进几句关于全球茶全产业链需要协调共同健康发展的建议!不是说吗?传播已经成了茶产业链不可或缺的环节了吗?
斯里兰卡茶叶在2012年、2015年遭遇高温干旱气候原因减产后,2016年又遭遇幅度高达11%的减产!斯里兰卡的茶叶仍然没有摆脱农产品种植靠天吃饭的传统原始的作业方式,虽然茶园主体以较集中的种植园管理模式为主,茶场场主主导了斯里兰卡的大部分茶叶生产,他们也是科伦坡茶叶拍卖市场的主要卖主,他们一直遵循也坚信拍卖是唯一公平的交易模式,习惯了这样的卖原料,等到斯里兰卡政府号召打品牌时,到现在还有点手忙脚乱地转变不过来!自主品牌的崛起,旅游+茶新兴茶体验模式的驱动,未来斯里兰卡完全依赖外贸出口的格局很快就会改变!
与斯里兰卡95%的茶叶用于出口相反,中国茶叶只有13.5%用于出口,主要是中国除了是第一大茶叶生产国外,也是第一大茶叶消费国,国内市场的持续旺销和增长,而出口卖价低廉和效益低下,导致不少生产者放弃了外销而选择国内市场。一个行业到了连从业者都要放弃了,这是必须要引起行业领导者的重视的。利用这样的机会,我们也把这样的现象写出来,希望那些来自消费国的茶媒体记者也对此进行思考!
茶世界,世界茶,从茶园到茶杯,或是从茶杯到茶园,只有一杯茶汤的距离!
下午去参观一家斯里兰卡的茶叶深加工厂。茶叶深加工领域,尤其是萃取技术下的速溶茶粉,内含物成分提取,不仅是斯里兰卡,连中国也一样,由于没有在终端应用的领域取得自主产品开发和产品的市场推广,这些深加工茶厂无不成了换了形式的原料供应商!做传统的红茶,是为立顿打工,速溶茶粉则为统一、康师傅打工!

